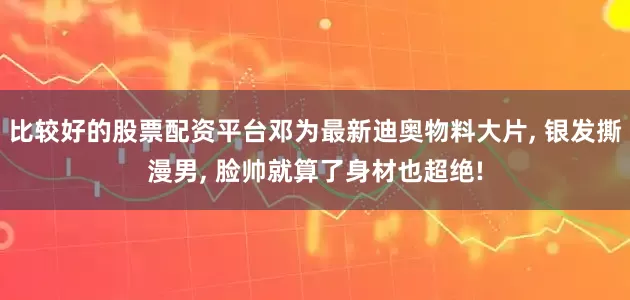1995年纽约的蘑菇云,到2025年喜马拉雅的黑烟:蔡国强三十年的漂泊与回旋


海拔五千五百米的风,不是普通的风。它带着雪粒,像刀子一样划过脸颊。江孜热龙一带,平日除了牧民和牦牛,很少有人会来——那天却聚了几十号人,架着设备、搬着箱子,在一个临时搭起的平台上忙碌。有人说这是“升龙”,蔡国强站在高处,比划着角度,他习惯用手势去丈量天空的位置,就像画布上的线条。


爆破声响起的时候,当地的小孩被母亲拉进帐篷里躲避,那片原本清透得能看到远山轮廓的空气,被彩色烟雾搅成了一锅粥。几天后,牧民才敢把羊群赶回原来的草场,但总觉得草叶上有股奇怪的味道。


倒回到1995年的纽约,一个初到美国不久的中年男人,在哈德逊河边第一次放出自己的“蘑菇云”。那时候他38岁,从福建泉州一路辗转日本,再跨过太平洋。他记得自己在上海戏剧学院舞美系读书时,西方现代艺术刚涌入中国——油画不再是唯一选择,于是他开始试火药。这种想法最早是在家乡老街的一次庙会看焰火时萌生,“要是能让它留下痕迹呢?”他后来对朋友这样说。


泉州地方志里有一句旧话:“市井之人好观焰火,以为吉兆。”老人们讲起八十年代末那个冬夜,说城南码头曾经被一阵实验性的爆破照亮,那也是蔡国强早期试验之一,只不过没人想到这会成为他的招牌技艺。


在日本,他遇见了吴红虹,两人在东京租住过一间不足二十平的小屋,小窗外就是电车轨道。他们在那里结婚,大女儿文悠出生——按当时政策,她拿的是日本籍。有一次邻居老太太送来一卷富士山明信片,说等孩子大些可以去看真正的大山;谁知道多年后,《升龙》的最初设计图就写了富士山的位置,只是没获批准。

纽约苏活区,他们换了一套顶层公寓,有个面向东河的小阳台,小女儿文浩在那里学骑滑板车。她长大后穿高定礼服走进巴黎名媛舞会,这类场合一般只认门第和血统,不认作品。当晚她发了一张模糊照片给父亲,上面灯光晃动,看不清人脸,却能看到吊灯下那条白色长裙尾摆拖地很远。

插叙一下2008年的北京奥运开幕式——鸟巢上空29个脚印焰火沿中轴线延伸,这是蔡国强最广为流传的一次创作。在福建老家的村口,他还为奶奶做过《天梯》,用烟花把钢索从海边一直引向夜空,据说完成那晚,有渔船停下来吹哨致意。但也有人记得更刺耳的一幕:九十年代末,他在长城尽头用了六百公斤火药搞所谓延伸项目,当地护林员第二天捡垃圾捡到手酸,还抱怨炸出的碎屑卡进石缝里几年都没清干净。

再切回喜马拉雅。《升龙》计划,其实1989年就在纸上成形,日本、法国环保机构都拒绝了。他自己承认,这是一桩憋了三十多年的心事,如今终于找到了落点。但落点选在青藏高原,让很多关心生态的人皱眉。这片冻土植被稀疏,一株小灌木可能要二三十年才能冒出几厘米,一旦受损,就像老人断骨,很难愈合。有环保专家提醒,高海拔低温环境下金属盐燃烧后的残留物分解极慢,“比乌龟爬还慢”——这是专家半开玩笑的话,却让当地干部听得直摇头。

调查组来了,说燃放前驱赶动物、事后修复环境,可牧民更相信自己的鼻子和眼睛:空气混浊、草叶变色,还有几块硬壳状的不知名碎屑嵌在土里。不止一个老人提到去年泉州无人机掉落事件,“都是一样,不想着改。”

吴红虹很少公开露面,她更多是在海外展览现场陪伴丈夫。从九零年代旅居日本开始,她就没有长期住过国内,大女儿文悠出版过一本叫《可不可以不艺术》的书,小女儿则活跃于社交圈。而这一家人的生活重心显然与国内相距甚远,所以当公众发现他们常住国外、大女儿持日本籍、小女儿美国出生,中国籍只留给蔡国强本人时,那种心理落差便加深了对《升龙》的反感:国外不能做,就回来挑敏感地点?

洪晃曾经隔着半个地球批评他说“不负责任”,这种话不像外交辞令,更接近茶桌上的直言。有记者翻出齐鲁壹点旧稿,上面写着他早期“地平线计划”炸废船导致鱼苗死亡,但当时网络尚未普及,没有形成舆论浪潮,如今不同了,每一次黑烟都会迅速扩散成影像证据,被无限复制保存下来。

至于这次调查结果什么时候出来没人知道,有人猜可能拖到冬季,也有人说查完也不会公布细节。在江孜镇集市旁的小茶馆里,一个背毛毯的大叔摇头笑:“你问我啊,我只晓得去年谷雨夜风怪冷,今年秋分又闹腾,你看,是不是命数。”

象泰配资-股票配资导航-炒股票加杠杆-股票账户怎么开通杠杆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- 上一篇:能加杠杆的炒股软件不同资料来源的伤亡数据存在显著差异
- 下一篇:没有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