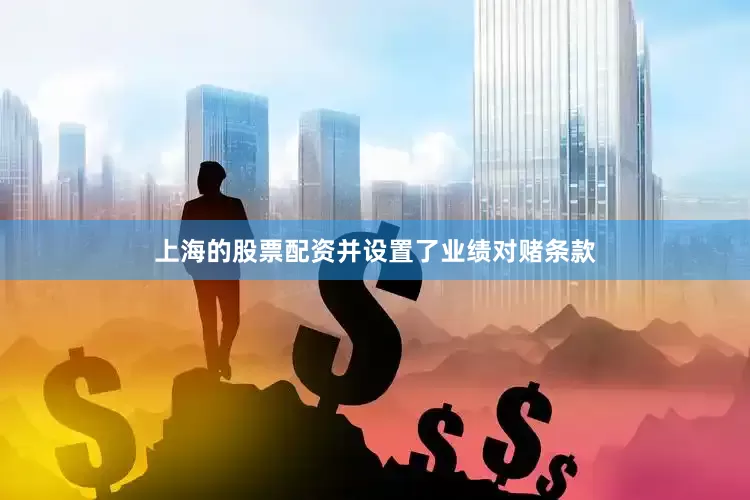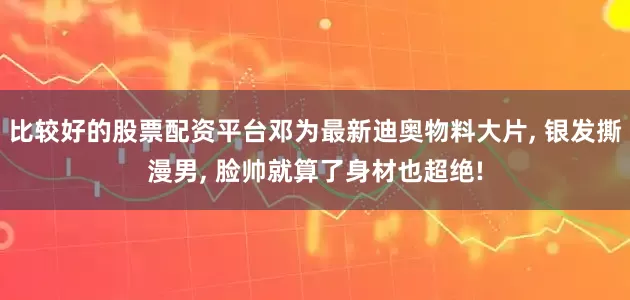《——【·前言·】——》
1944年1月2日晚上很晚的时候,有个脸遮着的女子突然跑到施亚夫家里,一进门就问:“你是不是共产党的人?”
家门大敞,城里的防御图就摆在桌面上,他的身份眼看就要穿帮,敌人说不定啥时候就动手。他只剩三天时间,这三天里得决定自己是死是活,还关乎着两千条人命呢。

【潜伏者的破局:1944年施亚夫深夜危机】
1944年1月2号晚上,施亚夫回到了家,他一回头,瞧见屋门留个小缝,有个蒙着脸的女人,嗖的一下,就窜了进来。
她一开口,施亚夫心里就咯噔一下:“你该不会是共产党吧?”夜里漆黑一片,他手脚冻得冰凉,只能隐约看到女人眼里闪着光。就是这一晚,关乎着他还有两千人的性命安危。

施亚夫32岁那年,已经是个手握大权的中将了。上头觉得他是个能干大事的人,下面的人呢,都觉得他是个厉害角色,不好惹。
他心里清楚得很,这个位子,那可是在刀尖上跳舞,稍有不慎,满盘皆崩。
他并非出身于汪伪政权,而是来自江西苏区,是个经历过战火洗礼的老红军。他上过战场,挨过敌人的鞭子,还曾在队伍中掉过队。
1935年,他在被围困时腿部挨了一枪,跟组织失去了联系。但他命大,没死成,反而通过假装成别人悄悄溜回了城里。
他不认命,也不相信忠诚能当护身符,他靠的全是自己的判断和实际行动。

1942年那会儿,组织又找上了他。他啥也没说多余的话,直接就问:“进去了,啥时候能动弹开干?”
回答是两年时间。
他应了一声:“行了。”
他是新四军安插在伪军里面的一个最关键的人物。
我从最基层的连长做起,仅用一年时间就升到了团部。接着,我又花了四个月,彻底搞清楚了敌军的电报发送规律、武器装备的分布情况,以及他们主官的行事习惯。
他很明白一件事:情报这事儿,根本不需要一摞摞的文件。有时候,一个动作、一个小误会,甚至一个眼神交流,就能救下一条人命。

他就是那个把日军的“清乡计划”传出去的人。
那时候,粟裕召集大家商量对策,会议地点定在了南坎边上的一个小村子,周围就那么几条窄窄的小路。
施亚夫得知了情报,琢磨出日军防守的打算,立马在当天晚上把电报发了出去。
新四军临时改道走另一条路回去,成功避开了敌人的埋伏。日军从四个方向包围的计划落了空,最后只抓到了几位当地的干部。
日军可不好对付,他们特高课里头的人开始动手查谁把情报给漏出去了,还翻起了以前的资料档案来查。
施亚夫心里咯噔一下,自个儿在军部大会上挑明了说,对那扫荡的地盘安排有意见,他讲:“南坎那地界儿对我们部队不利,一不留神就可能让人给埋伏了。”就这么着,他把大家的思路给带偏了。

他讲这话时,手里头攥着一小块冰。冰化了,手心都冒汗了,他得把话说顺,一点破绽都不能有。
但他心里清楚,时间紧迫,任何一个小细节被翻出来,哪怕是三年前那张通缉令,都可能让他悄无声息地消失。
特高课那一套,不看重啥证据,他们追求的是直接“动手”,而不是听你“啰嗦”。

【门缝里的杀机】
1944年1月2日晚上很晚的时候,苏中的一个小镇子里,风悄悄地沿着墙角溜达。
施亚夫刚打军区溜达回来,一进家门,屋里黑洞洞的。他立马感觉不对劲,屋里头的气温怪怪的,就像是有人刚在这儿喘过气似的。
屋门敞开着,窗户上糊的纸透出一抹身影晃动,他立刻转过身,发现屋里已经站了个女人。她围着围巾,袖子拽得老长,眼睛半眯着像是藏着什么。

施亚夫默不作声,悄悄地往抽屉旁边的灯绳那儿挪动。
那女的先开了腔:“别拽我。”
嗓音低沉而沙哑,听起来像是憋了很久:“你是不是共产党员?”
施亚夫心里猛地一震,但脸上依旧保持着那副官样文章:“搞错了,夫人。”
“你当真不认账?”
“施亚夫这名字,挺大众的。”他嘴角上扬,背后汗水已经把衬衣湿透了。
那女的挺镇定:“她1932年在瑞金当的兵,33年因为腿受伤就退伍了,到了36年又跑到上海去了,还用了个假名汪启斌……这些底细,日军那边全掌握着呢。”
她稍微停了停,接着说:“田铁夫现在也知道了这事儿。”

这不是在试探你,是直接告诉你,他的地位现在岌岌可危,就像风中快倒下的树一样。
屋里安静得吓人,远远传来狗叫声,而且越来越频繁。那女人撩起袖子,细长的手腕露了出来,她随手一摸,扔出个干巴巴的东西。
那是一张老旧的报纸,上头用红笔勾画出了他在江西时被通缉的消息。
在六号那天到来前,他们就会采取行动。话毕,女人迈开步子就走了。
门口再次陷入漆黑,地上的报纸微微晃动,就像是风儿轻轻拨动了悬挂绳索的感觉。
施亚夫挺沉得住气,他慢悠悠地坐下来,划了根火柴把烟点上,但也没急着抽,就是那么看着烟头一闪一闪的。

他得弄个明白:她到底是来救他的,还是想来取他性命。
要是真想杀他,肯定不会留个纸条,也不会提前告诉人家啥时候动手,这明显就是给个提醒。
他不能再拖了,立马站了起来,走到墙角,掀开夹层,把小电台掏了出来。
熟练操作调频设备,启动机器,输入密钥,发送电报:
身份有疑,敌人可能六号晚上到七号早上动手,咱们得提前行动,请大家给力。起义时间我看挪到五号一早比较好,用方案C。
比赛结束后,他没去关灯,也没躺下休息,就那么坐着,整整一夜没挪窝,两眼直勾勾地看着手里的报纸。他心里明白,这回是真的没有回头路了。

【起义与生死局】
1月3号一大早,天气冷得直哆嗦,施亚夫把军装穿得板板正正,每个扣子都系得牢牢的。这时,外面有手下问他:“师长,早饭是在营地里吃吗?”
他应了一声:“还是老样子。”
日子还是老样子,这就是最妙的掩护。

吃完早饭,他像往常一样去巡查营地。伪军三十四师的副官处长,王宜山,躲在营房的一个角落里,眼神不定,明摆着在跟踪他,藏都藏不住。
“王处长,来来来,跟我一块儿溜达溜达。”施亚夫这话一出,俩警卫立马一左一右把他架住,进了屋,咔嚓一下给他戴上手铐,接着就是搜身。
他兜里揣着两份日军军部的电报抄件,时间是六号大清早,第一页上头赫然写着要清除的名字:施亚夫。
他跟王宜山坦白:“我现在没法回头了。”王宜山默不作声,浑身直冒冷汗。过了俩钟头,王宜山最终还是签署了投降书。
到了1月4号晚上,事情变得更加紧迫。晚上七点钟的时候,施亚夫收到了一份邀请函。
今晚有个麻将局,田师长请您一起来玩。

田铁夫是三十四师的领头人,也是日伪混合军队里的关键人物。他掌控着一部电台,能指挥宪兵行动。那张请帖上没写名字,但他心里跟明镜似的,清楚得很。
这是一场安排好的事儿,他二话不说,按时就到了。
麻将桌上,坐着三位军官,还有一个日本顾问,茶水冒着热气,打牌的气氛挺悠闲。施亚夫摸了几轮牌后,猛地起身说道:“肚子有点不舒服,我得去厕所一趟。”
他走出屋子后,迈开大步匆匆前行,转进一条昏暗的小巷,接着悄悄溜出了军营的围墙。
过了三十分钟,营地最外头站岗的士兵手里被塞了张小纸条,上面写着:“留意三号库房,半夜会有情况。”
那就是反抗开始的信号。

1月5号早上四点钟,天还黑漆漆的,营地里的大喇叭突然响了,响的不是人名,而是起床号。
与此同时,三号库房门口停着的两辆大货车突然爆炸,火苗嗖的一下窜得老高。
在城门口那儿,杨海柱这个伪军司机其实早就是咱们的人了。他瞅准时机,掏枪就把站岗的卫兵给干掉了,然后上手就把城门上的大铁锁给拉开了,那城门就慢悠悠地打开了。
施亚夫和他的贴身保镖飞快地从指挥所冲了出来,队伍里没人等命令,大家都毫不犹豫地跟上。那一千九百多个士兵,几乎没有一个人往后退的。
他们心里明白,眼下这关头,要是留下来,那就等于等死。

用手雷挡住后边的追兵,火把扔向弹药堆引发大火,机枪架在路上阻断通行,一整夜的急行军,直接冲到了新四军的地盘。
天刚蒙蒙亮,苏中军区那边就收到了电报,说“三十四师已经回来了”。粟裕低声讲道:“他这回是押对宝了。”

【余波】
施亚夫突然之间就变成了新四军里的大英雄,可他根本顾不上喘口气。
刚回到队伍隔天,他立马穿上战袍,亲自率领队伍突袭了日军盘踞的荣阳镇,那正是他之前潜伏时一直暗中摸查情报的地方。
短短三个月,他一口气攻占了四座城池,新四军里的将领都称他为“拼命三郎”。

有人直接问他:“你害怕死亡吗?”他微微一笑,回答得很实在:“当然怕。但如果不采取行动,可能会死得更快。”然而,战场之外的那些后续影响,比子弹还要让人心寒。
潘宜娟,那个半夜溜进他家门的女子,之后再也没出现过。
有人传她被秘密带走,是特高课的人干的;也有人讲,她一溜烟跑去了上海;更有人议论,她本来就是共产党一员,只不过用了激进的法子,催着他早点动手。
施亚夫后来再也没碰见过她。有次,有人聊起了她,他好一会儿都没说话,最后就简单蹦出一句:
她帮了我大忙,可我压根不知道她叫啥。
打完仗后,施亚夫没停下脚步,继续打仗。他的职位升了,所在的队伍也变了,但他还是冲在最前头。他有这么一句话,好多战士都记在心里:
他们能把黑的硬说成白的,咱们还是得靠自己过日子。
这是他自个儿在漆黑一片的夜里,实实在在瞧见的。
象泰配资-股票配资导航-炒股票加杠杆-股票账户怎么开通杠杆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